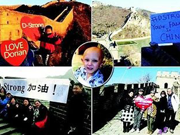國家食藥監總局遭遇“民告官”

圖/東方IC
1月26日,醫藥界出了一單“民告官”的大事!養天和大藥房起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強制推行藥品電子監管碼屬于行政違法,應立即停 止。而運營這個國家藥品電子監管網的正是一家商業公司。業內分析,藥品零售企業狀告國家食藥監管總局的背后,矛頭更多的是指向同業競爭。
1月1日起藥品全部賦碼
所謂的藥品電子監管碼是國家總局2006年開始建設的一個藥品監管系統,最初只用于特殊藥品監控,直到2008年又提出將其分類分批推廣到所有藥品,旨在實現藥品全品種、全過程、可追溯監管,防止假藥流入渠道。
2015年1月4日,國家總局的《關于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全面實施藥品電子監管有關事宜的公告》要求,2015年12月31日前,境內藥廠、進口藥品制藥 廠須全部納入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以下簡稱入網),在藥品各級銷售包裝上加印(貼)統一標識的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碼(以下稱賦碼),并進行數據采集上傳,通 過中國藥品電子監管平臺核注核銷。2016年1月1日后生產的藥品應做到全部賦碼。而所有藥品批發、零售企業,也要求2015年12月31日前須全部入 網,對所經營的已賦碼藥品“見碼必掃”。
如果企業拒絕入網賦碼,就有可能喪失參與藥品招投標的資格。而藥品零售企業拒絕入網賦碼,則無法獲得GSP認證。
推出以來反對聲一片
雖然,藥品電子監管系統的推出是出于實現對藥品實行全程可追溯監管的初衷,然而,該系統從推出之日起就引來反對聲一片。
養天和大藥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能表示,《藥品管理法》并未規定藥品生產者對所生產的藥品需要加印電子監管碼,也未規定藥品經營者對出庫入庫藥品賦 碼。“在上位法沒有修改之前,國家總局擅自發布文件,推行電子監管,要求藥品加印一家商業公司經營的電子監管碼,要求藥品銷售企業對購進和銷售的藥品都要 掃碼核注核銷并且將信息上傳至商業公司運營的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顯然,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也超出了法律對其授權的范圍。”他表示,1月25日,養天 和已經委托律師把起訴狀遞交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賦碼制度還被指存在既沒覆蓋全、又增加了企業投入的問題。 此前,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曾表示,電子監管碼只在藥企和批發零售藥店等生產、流通環節使用,而掌握藥品銷售量80%的醫院,未被納入國家藥監 局的電子監管系統。更重要的是,電子監管碼的實施還需要企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李能表示,僅僅藥品零售行業一次性增加運營成本初步估算為150億元,后 續每年都還有不菲的投入。
事實上,李能口中的“商業公司”,或許正是入網賦碼徹底“惹毛”醫藥企業的最關鍵原因。
羊城晚報記者在國家食藥監總局了解到,藥品電子監管平臺的技術服務機構是中信21世紀(中國)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也是國內拿到第一塊第三方網上藥品銷售資格證的試點牌照的企業。
這家“商業公司”經營醫藥業務,同時又運行著國家總局的藥品電子監管平臺。這讓國家藥品電子監管平臺的身份十分尷尬,更招惹了業內的不滿。
包括老百姓大藥房董事長謝子龍、一心堂總裁趙飚等在內的許多同行紛紛提出質疑,裁判員與球員的雙重身份可能導致不公平競爭和數據安全問題,要求立即停止藥品電子監管碼系統由企業運營的做法。
狀告背后或為同業競爭
不過,業內分析,藥品零售企業狀告國家食藥監管總局,更多的矛頭其實是指向同行。
李能質疑,通過藥品電子監管網的運營,這家“商業公司”能掌握和運用全國所有藥品經營企業的詳細銷售數據,其他藥品經營企業哪還有什么平等競爭的機會? 雖然這家“商業公司”屢次申明電子監管碼數據不會違規外泄,但近兩三年來,有一批信息或咨詢公司都在提供基于藥品電子監管碼數據系統的數據統計項目進行銷 售盈利,這些數據從何而來?
直至發稿時止,國家食藥監總局尚未就此事給予回復。
- 上一篇:國內止咳藥內含嗎啡在美被召回
- 下一篇:網爆:中國整容市場規模將達8000億元
- 10-11
- 10-18
- 02-27
- 10-11
- 10-18
- 10-14
- 10-14
- 03-13
- 10-17
- 精彩必讀